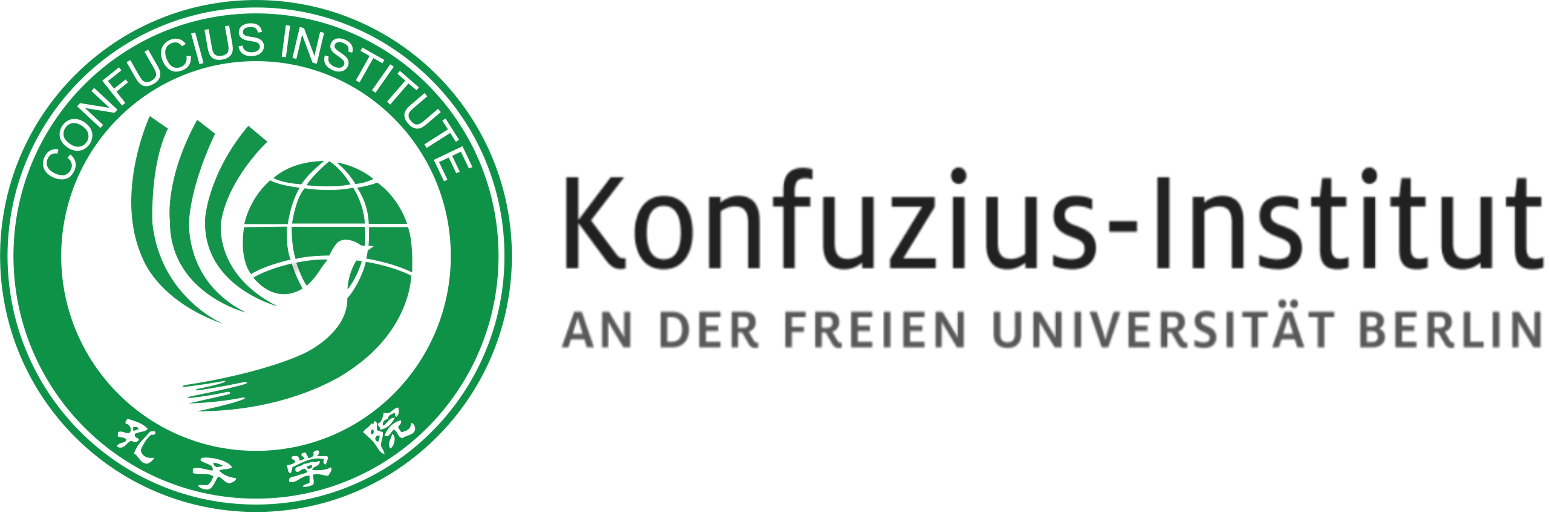海报5:虹口时期的童年
索尼娅·克里普斯于 1939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上海,于艰苦的流亡生活中长大。她的弟弟彼得出生于 1945 年 3 月,也就是战争结束前几个月。1939 年至 1945 年间,约有 300 名难民儿童降生,他们被称为 “上海宝贝”。这些孩子大多参与日常生活,与成年人一起劳作于每天的基本生活,包括打水和排队买饭。由于孩子们没有经历过逃亡阶段,他们对流亡的现实和虹口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体验一般远不如他们的父母深刻,毕竟他们的父母必须确保家人的生存。即使在后来关于流亡青年的报告中,这些家庭在上海的生活有时也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可选的冒险经历,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危难处境。
尽管流亡生活得为生计奔波,并充满不确定性,但其中也不乏无忧无虑的闲暇和玩乐时光。上海与其他国家的孩子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会玩 “过家家”,在其中模仿大人,玩球或捉迷藏。女孩通常还会玩流行的 “伊森多加”,她们会跳过由许多橡胶圈组成的绳子,同时会唱一种多语言的儿歌。男孩们则会玩弹珠。由于隔离区的路边公园只有一小块绿地没有几棵树,所以在流亡中出生的孩子们大多时间都在此度过,以至于对其他的城市街景一无所知。在马路上玩耍和随时随地哼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玩具是稀有且珍贵的,童话故事则是永恒的陪伴。这一点上,人们也相互帮助。比如,克里普斯一家在流亡中结识的歌剧作曲家利奥波德·马斯[1]为索尼娅创作了一本儿童诗歌集。一位友好的邻居从德国一直带着他的钳子,给索尼娅修好了她的中式旱冰鞋。
一些儿童上了由捐助者和援助组织成立的托儿所,而绝大多数儿童都上了学。由于母亲的工作关系,索尼娅·克里普斯于 1941 年进入了新成立的 “萨松·科莫尔国际委员会托儿所和儿童之家”,一家由护士兼幼儿园教师莱塞·阿申多夫负责管理的日托中心。在上海大亨维克多·沙逊的资助下,欧洲难民组织国际委员会名誉秘书保罗·科莫尔满怀仁爱地开办了这家托儿所。而其开幕仪式在《上海犹太纪事报》上获得了整版专题报道。 从 1945 年起,索尼娅·克里普斯在上海犹太青年协会(SJYA)学校女子班就读了两年,该校因其赞助人霍勒斯·卡多里而被称为“卡多里学校”,大多数在上海的难民儿童,还有一些中国学生都在此校就读过。该校于 1939 年在虹口区创办,由校长露西·哈特维奇[2]领导,目的是为越来越多来到上海的赤贫难民家庭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总共大约有700名儿童和青少年前后在这所学校就读过。
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学生将来会移民到英语国家。在虹口区,德语、英语、意第绪语和汉语随处可见。孩子们通常学习得很快,能在短时间内适应上海这个语言多样、社会多元的城市,比他们的父母更容易融入。丰富的教育机会和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多样性对许多孩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帮助他们在流亡后能够作为移民在其他国家重新适应生活。
[1] 利奥波德·马斯[1](Leopold Maass)于1939年6月离开柏林后抵达上海。逃亡中,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其中包括他的藏书和大部分作品。共计超过600首歌曲、插部、流行曲和轻歌剧。
[2] 露西·哈特维奇(Lucie Hartwich),曾担任柏林王子摄政街犹太教堂内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1938年“水晶之夜”后,她乘船逃往上海。在航行途中,她为同船乘客教授英语,帮助他们为抵达上海做好准备。这一举动给同船的商人兼慈善家霍雷肖·卡多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1939年11月犹太青年协会学校开学时,哈特维奇被聘为校长。
图片注释:
1) 克里普斯一家在上海,摄于1945年。
2) 手绘儿童书籍的第一页,附有利奥波德·马斯的题词。
3) 索尼娅和彼得在草坪上玩耍,摄于1946年。
4) 1941年4月27日《上海犹太纪事报》上“儿童之家”的报道。
5) 索尼娅·克里普斯在做体操;彼得·克里普斯与邻居家的猫和玩具(欧洲娃娃和熊猫毛绒玩具)
6) 索尼娅·克里普斯(倒数第二排,从左数第一位)在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学校女子班,摄于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