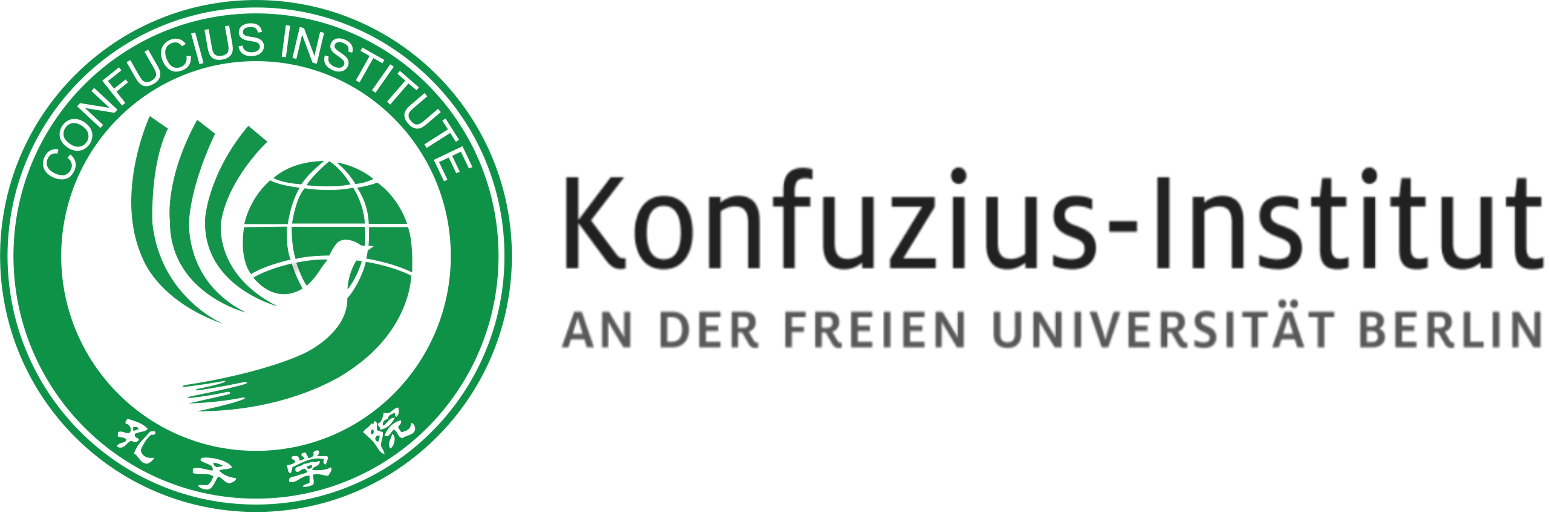海报4:流亡生活的日常
流亡生活充满贫困与不确定,唯有坚韧才能支撑度日。大多数人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们依靠犹太组织的援助存活,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医疗援助。许多人不仅身无分文,还要在没有语言技能或工作背景的困境中摸索生计。尽管如此,社区内部还是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一些人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其他人则在援助项目中工作,或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
赫尔曼·克里普斯抵达上海后,立即投身于各种工作,努力为家庭维持生计。他曾在“上海欧洲犹太难民援助委员会”担任三个月的英文和德文通讯员,也短暂尝试过做面包师。后来,他开始为一位中国商人销售鸡蛋,并在过程中学会了上海话。伊尔莎则重拾起在德国接受的裁缝技艺,为其他难民缝制衣物,以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她曾在一家裁缝铺帮工,换取每日三餐,并由此为女儿争取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名额。这对克里普斯一家来说尤为关键:约7 个月大的时候,索尼娅·克里普斯得了严重的痢疾。儿科医生卡尔·莫斯[1]直接给她输了她爸爸的血,救了她一命。医生拒绝了任何报酬。
当时的工作多以非正式的方式组织进行。服务与物资常常通过互相交换来获得,人们在后院或住所附近开设小本经营。社区成为生存的关键支撑:会缝纫的人为邻居改衣做衣,有食物的人则在邻里之间分享。尽管贫困与不安随处可见,这种巨大需求下的互助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团结型经济。在条件艰苦的虹口,难民们还建立起基础的护理与教育体系——犹太学校、社会服务中心、医疗救助点逐渐形成。许多难民在这些机构中上班或打零工。
粮食是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口粮匮乏,许多难民只能靠极少的资源度日。犹太援助组织会分发大米和简易的汤食,但饥饿依然如影随形。许多难民在屋后开辟小菜园,自种蔬菜,也有人尝试与中国邻居做小本买卖,用以应对食物短缺的情况。烹饪通常是在涂有粘土的小炭炉上进行,燃料是自制的 “蛋煤”,即水和煤渣的混合物。
1943 年 2 月,隔离区的建立以及与此相关的虹口强制搬迁意味着难民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社区在确保难民生存的同时,还努力维持一丝日常的常态。孩子们上幼儿园、上学,人们开设咖啡馆和小商铺,借此重现故乡的气息。邻里之间彼此扶持,一同学习手工艺技能,组织文化活动,庆祝犹太节日。对于家庭来说,为孩子们维持一种日常生活也很重要。这样尽管未来前景不明朗,他们也能体验到一种稳定感。
[1] 卡尔·莫塞(Dr. Karl Mosse),1896 年 9 月 21 日出生于柏林,医学博士,儿科专家,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婴幼儿保健中心主任。1933 年或 1935 年移居上海,担任儿科医生。
图片注释:
1) 1944年颁发给赫尔曼·克里普斯的居住证明。
2) 日本占领当局于1943年2月18日发布公告,宣布设立难民隔离区。
3) 伊尔莎和索尼娅在上海虹口区家窗前,摄于1940年左右。
4) 印有索尼娅照片的“索尼面包”包装纸,由赫尔曼·克里普斯和一位化学家共同设计和生产。
5) 索尼娅·克里普斯(右二)在“萨松·科莫尔国际委员会托儿所和儿童之家”,摄于1943/44年。
6) 索尼娅·克里普斯的儿童身份证,由欧洲难民组织国际委员会签发,有该组织名誉秘书保罗·科莫尔的签名。